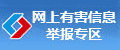长江商报消息 平时公务员,周末写小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本报见习记者唐诗云
提到张楚,很容易让人想到那位著名的歌手。然而,与歌手用声音表达不同,这里的张楚,选择的是文字,并且坚持了许多年。白天,他在县城税务局上班,业余时间他写小说,作品刊登在《人民文学》等著名期刊。2014年,他的短篇小说《良宵》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2015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秘密呼喊你的名字》问世。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爱喝酒、爱玩,却除了求学以外没离开过家乡,他喜欢和朋友聚会,却也可静心来写长篇。他身材高大却长一双小眼睛。
近日,作家张楚接受了长江商报记者邮件采访。
佩服始终膨胀荷尔蒙气味的作家
记者:你用了6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才给自己一个交代。访问你之前,我就觉得你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看完你的新书《秘密呼喊你的名字》,里面写到高考失败想自杀那段,发现其实你内心容易忧郁、敏感,我几乎能听见你成长的声音。
张楚:(忍不住笑了)其实你对我有些误解。我是个随意、安静的人,很多时候被拖延症折磨,真正有野心的人从来都是当机立断、连做梦都在往前冲的。有时我会想,之所以能够坚持写作20多年,主要还是出于纯粹的热爱。这种热爱或许是骨子里的、与生俱来的、偏执的。不过,我觉得敏感和忧郁对一个写作者来讲很重要。只有长了第三只眼睛,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细节,只有长了第三只耳朵,才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故事。另外你说得没错,我是一个有秘密的普通人,一个喜欢读书、写作的小公务员。我喜欢平静如水的生活,看起来波澜不惊,其实水面之下激流跌宕。
记者:你最喜爱的作家是苏童,模仿他写了十几万字的小说。你喜欢一个作家,就会系统地研究他的所有作品和访谈,是什么让你对写作充满了热情?
张楚:每个写作者在写作初期都有偶像。这跟歌迷喜欢特定的歌手是一样的道理。我阅读苏童的作品是在大学时期,看遍了他所有的小说,梦想着有天能成为跟他一样优秀的作家——这个愿望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了。他一直是夜空中最亮的几颗星之一。其实当时喜欢的作家还有很多,比如格非、余华、阎连科、刘震云、方方等。从最初庞杂的阅读中寻找自己喜欢的作家,是件开心的事。除了深谙他们的作品,你可能还会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常态产生好奇。我很佩服那些几十年如一日地写作而且作品中总是膨胀着荷尔蒙气味的作家。
记者:一般认为税务工作的标准有三个:真实,准确,微妙。感觉你的散文好像也是如此,真实、真诚。
张楚:你总结得很有意思,税务工作中常见的标准确实是真实和准确,至于微妙,可能需要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去理解吧。我的散文体现了我最真实的想法,可以说是灵魂中最赤裸的部分。说实话,我很怕有人去读,然后对我说,哦,原来你的本性是这样的。写小说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小说是完全意义上的虚构,我从来没有在小说中投射过自己的影子。那是一种安全的、舒适的表达方式,因为你就是那个无所不能的上帝。
对太强的故事性有种本能的抵触
记者:你在新书里几次提到苏童对你的影响,具体是哪些?
张楚:通过大量阅读苏童的小说,让我知道了小说是什么,小说应该表达什么,小说如何表达潜在的自我。我喜欢苏童的语言。那种准确、暧昧、潮湿与华美,可能是当代汉语最美的一部分。
记者:从小说《樱桃记》《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样黑下来的》《野象小姐》到您的散文集《秘密呼喊你的名字》看得出你的努力,试图将孩提时的梦想以文字的方式延续下来。还会有另外一个题材吗?
张楚:我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我身边的人,他们多多少少有些我的亲人、我的朋友的影子,还有一些,则是道听途说的人。他们孱弱的肉身形象总是和人们口头传诵的虚拟形象有着质的区别,即便我是个聋子是个瞎子,某段时间内,他们的故事也会让我变成一个耳聪目明之人。《七根孔雀羽毛》、《樱桃记》等是这些事件的入炉再造。
另外,我喜欢日常生活的诗性,我觉得这种单纯的、无意义的诗性会让复杂斑驳、乱象丛生的故事变得高贵、优雅、从容。在《七根孔雀羽毛》里,我让宗建明摆弄着廉价的孔雀羽毛,而在《细嗓门》中,我赋予屠夫林红最大的爱好,则是用猪下水沤的花肥浇花。说实话,写下这些细节时,很大程度上,我感动了我自己。
坚持写作完全出自热爱和盲目的自信
记者:你让我想起一句侯孝贤的话:限制的地方就是自由的开始。据说在两种场合最能看人性:一种是一个人很饿的时候,一种是一个人吃自助的时候。在你的身上,我们看见你的这两种状态。不管境遇如何,你始终不高不低。
张楚:这个问题有意思。我一直在县城的国税局工作,当过税收管理员,当过秘书,也当过党务工作者,这些工作是体制内的,但是与写作毫无干系。写作对我来说,纯粹是种业余爱好,因为是爱好,才不会抱太多期望,能坚持写这么多年,前面也说了,完全出自热爱和盲目的自信。
记者:我以为作家都是很感性的,但是我感觉到你很理性。
张楚:其实我是一个感性胜于理性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必要的理性是我们生存的必要条件,但是日常生活之外,更多的是对时光、对故人、对消逝的美好事物的感性认识。我觉得一个作家不能很理性,也不能过分感性,他必须处于一种中庸状态。前几天重读美国作家约翰·契弗的小说,觉得不如以前读起来完美,就是因为觉得他过于感性。我把这种感性称之为“廉价的感性”,当写作处于“廉价的感性”状态时,作品的品质就会感觉到某种甜腻和天真。
记者:你觉得中外作家写作方式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张楚:我觉得中外作家在写作方面的最大差异,是国外作家的写作生命要比中国作家的写作生命长。他们大部分从青春期一直到古稀之年,都会保持旺盛的创作能力,杜拉斯70岁写出了《情人》;菲利普·罗斯70多岁了,还写了《垂死的肉身》、《反美阴谋》、《凡人》、《愤怒》、《羞耻》等6部长篇小说;阿摩司·奥兹70岁了,还写了长篇《咏叹生死》。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比如爱丽丝·门罗,莫迪亚诺……但是国内的作家,70岁以后基本上写不动了。我想,这除了跟民族间体质、基因上的差异有关,可能更跟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有关系,具体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也说不清。我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持健康的、自由的生活方式,保持写作初期那种元气充沛的状态。
采访对象供图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