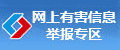朱幼棣。出版社供图
长江商报消息 我们能留给后代的只是地图上的线条和墨点,曲折蜿蜒缠绕的蓝色,清晰又遥远。祖祖辈辈留下的流淌了千年的大河小河,在我们这一代永远干涸了,消失了……”前地矿工作者、前新华社记者、前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朱幼棣在他的最新著作《怅望山河》中发出这样的忧叹。
这是朱幼棣继《后望书》之后,历时五年推出的又一部震撼人心的力作。日前,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以新书写作为主题,对历史与地理、成功与失败、长远与短见等谈起自己的一番见解,也聊到了对后三峡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诸多思考。
怅望山河,我们已经失去得太多
20多岁时,朱幼棣在矿山做技术员,每天在野外测量或到井下放样,自学了所能找到的地质与成矿的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供职于新华社,曾跟着国务院环委会走遍了大江南北,先后采访过淮河、海河、辽河和太湖、白洋淀、滇池等重要河流湖泊的污染治理。
青年时的人生经历以及后来的职业,让朱幼棣对地质的兴趣与爱好一直没有中断。据他的记忆和研究,生态的巨变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也就是半个世纪,两代人的时间,我们国家大地上许多河流湖泊干涸了,消失了。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灾变,是几千年来所没有的。
从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到北京缺水、海河断流,从南水北调的河区危机到天津的“无津”,从白洋淀污染的悲鸣到新安江水底被迫沉入的千年城池,从三峡天气的影响到鄱阳洞庭的生死……长期关注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朱幼棣,放不下对社会的那份责任感,回望历史,剖析当下。
诚如他所言,这些年来,怅望山河,我们已经失去得太多,而且这种破坏性的开发利用至今仍在继续。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欲说还休,不是一句重现“青山绿水”所能了断的。自2008年起,他动笔写作《怅望山河》,讲述了属于中国河流山川的失意与怅惘,试图找出导致这些现状的根源。
水危机、河水断流、地震不断背后到底是何种原因?一项项大工程是不是“功在当代”,却愧对子孙?如何正确处理闸坝与生态的关系?朱幼棣在书中以冷静、严谨的笔触,对有关生态的那些被隐瞒或者被忽略的重要真实做锲而不舍的追问,对现存问题和缺憾进行科学的观照。
“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中,除了政治觉醒、思想解放外,我想不可或缺的,是人的科学觉醒。”他进一步探问了“科学的缺失”,指出人类要有所约束,兼顾各方面利益,兼顾人和土地和山林自然的关系,这就是后工业化时期生态文明最核心的问题。本报记者 卢欢
朱幼棣,学者、作家。曾为新华社著名记者、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现为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研究员。
朱幼棣在经济、地质、能源、医药、文学甚至书法等诸多方面有较深研究,出版过十多部著作。《怅望山河》是继《后望书》、《大国医改》后又一部力作。
能否拨开大地震的若干疑云?
汶川5·12大地震撼动了中国和世界。
人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向岷江那条蒸腾着开发热浪,建有一座座梯级电站和不少高耗能工业企业,而地震中霎时又成为死亡之路的峡谷。开始是对紫坪铺水库受损,会不会影响下游城市引起民众的担心。但大坝基本稳固,现代工程已经表明了其质量的可靠。
随着生死救援,生死接力艰难展开,震中映秀逐渐“浮出水面”。映秀、漩口均位于库区。于是出现了质疑的声浪,紫坪铺水库是否与触发或诱发汶川大地震有关?
问题如此尖锐严峻,这可不是任何人担当得起的。与巨灾大难牵扯上的可能都意味着承担责任。
四川省有关部门急忙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紫坪铺电站与汶川大地震无关。一位专家断然说,怀疑紫坪铺水库诱发8.0级地震是没有道理的。
还有一位专家的说法令人相当诧异:“可惜紫坪铺水库没能诱发大地震,如果紫坪铺水库具备了诱发地震的种种条件,那么,遗憾的是晚建了几年。如果早建几年,使汶川地震应力的能量提前释放,地震造成的破坏就会比今天小得多。”
——这不仅是无知和轻薄,也是媚世无节的表演,是对人类良知和科学精神的亵渎。无忌的只能是童言,对于有相当职位职称的以专家自居的人来说,不能出口狂言,要知廉耻和进退。
试想,一个里氏8级大地震应力的积聚,需要几百年甚至数千年——离映秀镇距离最近的一次汶川6.5级地震,发生在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你用建水坝引发小地震去释放龙门山断裂带中段的能量,提前几年时间够吗?你打算是在明朝还是唐朝去建这样百米高的大坝!?——即使十年二十年前去“诱发”,也是高烈度的强震无疑。
(《怅望山河》选摘)
■访谈
我希望自己的写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锐读:早在2008年出版的《后望书》中,您就讲到了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也涉及一些江河水利工程存在的问题。为何时隔五年后又推出这本《怅望山河》,继续关注山河和文明的关系?
朱幼棣:《后望书》主要涉及西北的水资源、大调水,以及黄河三门峡水库等。那些年,我在西北走得多,对那里的情况了解也更多一些。三门峡工程争议比较大,我是从“无水的淹没”,即修大坝高度的误判的角度,对潼关等历史文化名城造成的毁灭性破坏进行了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损失都是不应有的,也无法弥补。可我们对这些失误一直都没有进行过总结、反思。
《后望书》出版后反响较大,我应邀在中央党校、浦东干部学院、北大等做过讲座,在深圳等社会大讲堂也讲过课,内容不尽相同。于是,每次都要花时间准备。记得一次讲课的题目是《河流与文明》,便涉及了陇东高原、汉水走廊。
锐读:后来,您对于祖国山河的研究更加深入了?
朱幼棣:确实,我这几年通过大量阅读和历史资料查阅,加深了对我国山河的了解,对近几十年来生态环境的突变深感忧虑。《后望书》中对长江三峡、长江中下游水系的生态变化等没有涉及,因为当时大坝刚开始蓄水,生态变化还不明显,而我的研究也欠深入。而在《怅望山河》的漫长艰苦的写作过程中,从更广阔的视野中去寻找答案,自己的思想也进一步成熟。
锐读:这本书里史料和资料征引得多,但又不掉书袋子,下笔严谨,解说详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朱幼棣:我的写作与报告文学不同,这是一种涉及一定专业领域的思考、研究与写作。题材比较大,而提不同意见亦很敏感。有些问题可能大家都看到了,感觉到了,但不一定能说出关键所在,而用情绪化的语言,又可能适得其反。因此,要在大量历史和现实的资料、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研究分析,才能得出结论。我希望自己的写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除了寻觅自己的记忆外,对未来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也有好处。
锐读:可能很多读者读此书前,没有任何关于水利、地质方面的知识,只有修建过多的大坝不利于生态平衡、汶川地震不应该死这么多人之类的肤浅认识。您是希望通过这本书还原某些被隐瞒或被忽略的重要真实,让他们对大自然有所了解?
朱幼棣:确实,有些专业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隔得比较远,但又可能和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比如水、比如空气,比如地震。我想延伸的科学、文学阅读也是必要的。我自己亦然。我喜欢的一本书是《人之上升》,也是一本英国人写的科学史,具有政论色彩。真实是作品的生命所在,被忽略和刻意隐瞒了的真实,往往孕育着自由与科学的思想,也孕育着真理。
锐读:这些年的研究和写作让您渐渐感到,回望和思考可能开始得太晚,而且还是民间性质的。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对过去发生变化的叙述与追问,保留这几十年间的山河记忆,其价值在哪里?
朱幼棣:确实,体制内有不少优秀的人才。但体制又分解成行业、部门、单位,这我前面已经说过,知识分子极易造成对体制的依赖,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1980年代初,发生过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由此引发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但对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方法路径、经验教训,一直没有进行过反思和总结。发展对投资的依赖,投资对资源的依赖,高强度开发扩张所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至今未有穷期。而当下能在资源能源行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多是国有企业。利益攸关,他们发出的声音自然强大。个人的能力和声音确实微弱、有限。但我想,资源狂欢的盛宴,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当下,中国经济的拐点可能正在出现,发展的严峻转折和转轨也在逼近——或者诞生新的经济制度和科学体系,或者永远不能。60年,或30多年,许多已经淡忘。我想,这两本书漫长的叙事和其中的思考,能与一些读者分享,亦能给后来的治史者作一些参考。
一部“江河史”
锐读:您说在写《怅望山河》时,老觉得是在写“江河史”,这就是江河的最后一章了。现在我们的江河究竟是何种处境?
朱幼棣:应该说,北方的江河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断流和枯竭;中部地区和南方河流主要是污染,而且许多地方地下水不能饮用。写北京水资源和海河这一章的时候,我深刻地意识到华北平原上已经没有长年流淌的河流了。海河的干流和主要支流,全都成了季节河,在地图上都应该标为虚线。滩地无水,平原上浅层地下水得不到补充,越来越深的机井破坏了含水层,不断扩大的漏斗区,使华北的生态系统进入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恶化之中。
这是一个多么严峻的现实啊!可作家们应邀组团去采访采风,还在讴歌调水工程、讴歌高坝大库。我觉得和他们格格不入。我写作不是为了评奖、赞助,虽然过去也写过小说,但现在早已放弃了虚构和个人化的纯文学写作。生在剧变时代,翻天覆地并非一味值得赞美。我们国家民族,需要有忧患意识。
锐读:这本书的前三章在追问大地震的预报问题。您认为在汶川大地震中有一些行业和部门是缺席的,如果不迎难而上,也许中国地震学的断代自此开始。为什么这么说?
朱幼棣:一是地震科学的发展问题。地震能不能预报?现在不能,将来能不能?必须面对,必须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这决定地震地质、地震监测和预报作为学科,今后如何发展。我不是“业内人士”,但在研究和写作中,了解了很多内情和详情,并没有全部写出。另一个问题是,汶川大地震的震中在映秀镇,在紫坪铺水库的库区,与高坝有没有关系?是不是水库诱发的?能不能完全排除?众皆缄口沉默,我想还是应该追问,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果地震科学不迎难而上,其前景实在不容乐观。尽管大地震几乎已被人们遗忘的今天,我认为这些问题仍然重要。我们必须与发生灾难的江河大地重建关系。
锐读:据最近的报道,地下水危机凶猛来袭,全国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地下水超采区总面积达62万平方千米。据您分析,这会造成什么后果?治理起来需多大代价?
朱幼棣:地下水资源的危机,是继江河水危机之后出现的更加严重的危机,危及子孙后代。地表水和地下水是互相转化的。但深层地下水的形成,可能需要几千年,甚至上万年。地下含水层破坏后,是不可逆转、不可修复的。江河地表迳流的变化,过度开发,首先影响的是浅层地下水枯竭。过去,由于技术上的限制,井不可打得太深,现在五十米,一二百米的深井都不费劲。用几千年上万年形成的地下水,去灌溉几个月一季收割几百斤小麦,就像用油去换水,用金子去换铜钱。实在悲哀!如果我们的河流不能恢复哪怕最低的生命流量,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转换不能形成良性循环。在工程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不能自己制约自己某些欲望,中国的地下水资源危矣!
有时只隔着一张纸,
点的人多了,
窗户也洞开了
锐读:在您看来,在许多水利工程建设上,缺少全流域的科学规划,缺少长远的战略眼光,许多恶性循环都根植于“传统”思维,重复一种简单的工程模式,无论其起始多么伟大。这样说,问题该如何避免?
朱幼棣:是的。我想应该从指导思想的改变与确立开始。如何做到人与江河和谐相处,合理有节制地开发利用。比如,我认为毛主席提出的“一定要根治海河”,在总体缺水的华北,因为1963年一场大水,把洪水和水灾当作主要矛盾进行“根治”,指导思想就是错了。在根治之后,洪水没有了,河流湖泊也干涸了。接着便是不断地长距离调水。所以,对任何一条江河,如何总体地把握、全流域的科学规划和合理的利用,显得尤为重要。而现在无序的开发利用,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北方几乎有河皆断,南方不少地方,有水皆污。活在当代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都往往有一种疏离感。其实,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正是我们的江河所养育的。
锐读:您看不惯如今专靠打横炮、抄捷径成名的专家,感叹大师的缺失。在您看来,李四光、郭守敬等大师给后世留下了什么财富?
朱幼棣:专家在当下不少民众的眼里成了贬义词。国家也许不缺乏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业内的专家,但缺乏有人文精神和广博知识的大师巨匠。专业和行业,部门和单位,成了职业和营生的需要。专家不可避免地成了行业、部门和单位的代言人。当然,行业部门的利益,有些与国家、人民的利益相同,但更多的并非完全代表民众的利益,这就需要超越。作为科学家,首先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郭守敬、李四光这样的大师,当下的大学是培养不出来,科技“孵化器”孵化不出来的。逝去的大师已不再归来,但中国却需要自由的学术思想、独立的科学精神,需要大师和巨匠。
锐读:您在后记《一个人的科学觉醒》中,唤醒科学精神的回归。在这样一个处于大变局之中的社会里,一个普通人的科学觉醒是否还需要一个过程?
朱幼棣:现在的年轻人科学文化水平普遍很高。这从地摊上卖的盗版书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有时只隔着一张纸,点的人多了,窗户也洞开了,清新的风就流了进来。
锐读:您看过对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在《江城》中对长江三峡的观察。“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历史,一边是自然的,另一个——尽管结果不——却一直循着直线往前:进步发展、控制。中国这个国家早就习惯了做出困难的抉择,而这样的抉择可能美国人连想都没想过。”您怎么理解他的这种总结?
朱幼棣:《江城》这本书是一个美国青年人写的,记录了他在涪陵“支教”几年中的所见所闻。他的详尽观察记录具有人类学的价值。 我看此书后想,生活在剧变的时代,一年全国出书无数,有能几本留得下的?怪不得古人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 彼得·海勒斯说得比较委婉,这种习惯的抉择,也许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思考方式的延续吧。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责编:ZB